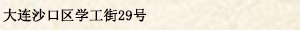走进佛教之七因果异说以因果为线索总
自由与良序·走进佛教·因果异说
天佑
因果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先就习以为常的现象界来谈,也就是一般科学范畴所说的“因果”。客观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许多因素先后相继、彼此制约。其中,引起一定现象的现象(产生的源由或动力)是“因”;由“因”的作用、“缘”之串联所引起的现象为“果”。如《大乘止观》云:“招果为因,克获为果”。简单地说,凡“因”、“缘”所致后“果”,如果其间在逻辑上有必然关联(连带关系),就形成因果关系。(《辞海》:“因果是一种连带的关系;其中‘因’是一事件之所以能产生的根源或动力;而‘果’则是事件发生后的状态。当动力与状态在逻辑上有必然的关联时,所形成的规律称为因果律。”)
其次,世间万物“普遍联系”,很少有“单一因”的情形出现;许多结果必要得到各种前因的支持。所以在“唯识学”中有“十因”、“四缘”、“五果”之设计,都是为因应繁复情况的说明。比如烧水:表面看来,把水加热是因,水温达到一百摄氏度(沸腾、气化)为果。然而,加热是水沸腾的主因,而不是唯一因——还有大气压强的作用。若压强不够,纯水很难达到一百摄氏度的沸点。于是,大气压强与温度都是因;至于哪个才是主因,那就要看认定的角度了。所以,在谈论“沸点温度”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大气压强”等因素(作为参考与标准);否则,在高海拔(低气压)或者高气压环境下,谈论沸点温度没有丝毫意义。
(西方哲学中有关于“因果关系的产生如何可能”问题的讨论。譬如英国哲学家休莫,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认定“因果律”不过是“心理作用”的结果——“事物恒常会合与心灵的习惯性联想”。他以为:在知觉经验中,若几件事常常前后发生——似有关联,即会在思维层面造成惯性联想,将之联结,断定有因果关系——当前事发生时,意念会自然期待后事发生。休莫的说法使其深陷“怀疑论”中;此外,更是摧毁了因果论的客观性基础。康德、叔本华等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因果性”归属于“知性关系”范畴中;认为因果观念是“知性”的“先验认识形式”,具有客观必然性,从而重建了因果关系产生的可能性。)
人类在原始社会阶段,唯为生存打拼;无法解释自然现象,又必要依循其规律,逐渐产生对“未知力量”的敬畏之情。(这是最初的信仰,导致宗教、艺术与哲思的萌芽。)有经验的长者传授“技巧”,似能总结“经验”,减少损失而能避免天灾;这样的部落会产生对“耆老”与祖先的崇拜及景仰之情(“大禹治水”)。相反,若先辈经验不足,或者灾难过于强大,使得部落损失颇巨,便会将畏惧心理放大,从而发展出自然神信仰(“诺亚方舟”)。自然神以力量为胜,祖先灵(部落神)以经验(知识)为胜,导致人类社会文明的不同发展方向(教、治二权的深层心理基础)。两大信仰形态全都存留下来,成为人类诸多文明的共同的基因。
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能力提高,剩余物资出现,部落产生崇祭行为——这是人类所能“找到”最基本的生存(因果)法则:讨好神灵;并且相信冥冥之中会有一股神秘力量,可以令人趋吉避凶。反映出人类对于无奈现实的投机与侥幸心理。(这里有一个前提:“全息理论”;认为万事万物之间全息关联,是一个彼此“关照”的“统一整体”。)这体现在古代原生文明的信仰情况:神灵主导一切,顺从与祭祀成为必要之重。此时的宗教行为仍然具有原始性、单纯性的特点——全为“信仰”服务,比如对“自然神”与“万物有灵”的崇拜。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了生活、生产与公平正义,因而在不同地域发展的文明有着相当雷同的表现。
例如古埃及人非常崇敬主宰尼罗河与收获的奥西里斯神;甚至视其与太阳神同等重要。(尼罗河每年都有水位下降的时候;大家便会举行仪式,象征性地让神“复活”,以此带来“生机”——未来一年的丰收。他们认为:奥西里斯带来了繁茂;“重生”意味着物产增加与灾难远离。)相类似的,我国自夏代起就有了“祭祀*河”的行为;同为农耕文明,对“母亲河”有着一致的敬意。古人对于自然现象与规律无从掌握,但渴望过上好日子的心情是共通的。只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民族的生活经验与社会形态各异,再加上彼此的侧重演绎,造就出千差万别的民俗传统与信仰形态。(是非善恶的原则大同,只是表相有差。)
九柱神系图随着大规模迁徙的发端,部落融合,文化交流,社会组织趋于复杂,贵族统治(剥削)阶级出现。他们为了管理需要,对宗教改造,开发出具有人格的律法神信仰;将“神灵世界”与人类生活刻意联系起来,企图消弭或者缓解阶级压力与社会矛盾。如此,具有伦理色彩的宗教便有了社会性。(文明进步,社会发展,导致“规则”的修正;这有其内在之逻辑与因果。)美国威廉·麦克高希在《世界文明史》中说:“任何社会中人对神的信仰通常都会跟社会正义连上关系。”上位者通常的做法是积极宣传“死后世界”与“冥府审判”,然后尽可能得与统治阶级的意志、现实生活的一切连接起来,以此威慑所有被统治阶级的“非分”之想。
譬如古埃及的《亡灵书》中关于“冥间审判”之记载。(《亡灵书》名义上是给“亡灵”看的,类似“作弊”行为;可实际上更像是一本提供弥留者阅读的类似“临终关怀”的“死后指南”。)当人死亡,他的灵*即脱离肉体,被引领至冥府,等候审判;无论法老、祭司、贵族,还是底层平民百姓,无不例外。大家全都渴望得到“冥王的恩宠”——获得永生、避免责罚,所以才会出现木乃伊与《亡灵书》等。祭司将经文抄写在坟墓里,让死后的人能够“照本宣科”,以此避免误入歧途或者触怒神灵。不过,这种“高消费”肯定不易普及;所以,此一“窍门”往往专属于统治阶级。(“受众”选择,成为贵族集团保障其地位的手段。)
《亡灵书·他行近审判的殿堂》说到死后审判的过程与细节:“当你被放在天秤中,用真理的羽毛来称量。”“神圣的众神,云一样地即位,抱着圭笏。在掂量词语时,请向奥西里斯把我说得美好;把我的案卷提交给四十二位审判者,让我不敢在阿门提特死亡。”那里有一个天平,两边分别放上死者的心脏(思想、意识、记忆、灵*)与象徵“玛特”的羽毛。如果死者作恶太多,心脏会下坠,被怪兽——阿姆特吃掉——从此便不得“超生”;若有小的罪过则须忏悔,以求获得宽恕。如果能被众神许可,“他被宣告为诚实”,即可获得“重生”:“登上了拉的小舟”,回到众神的国度;前往朝觐复活之神——欧西里斯,由其“赐予永生”。
这里提到:“被众神许可”与“用真理的羽毛来称量”,意味着要想得到永生,他的行为必须合乎“玛特(秩序、真理)”的规范。“玛特”被解释为“规矩”的象征:只要个人行为遵守神所建制的秩序,就能得到好回报。“行为受人喜欢的人会得到正义,行恶事者则受到惩罚;生命被赐予和平者,死亡将被赐予犯罪者。(莫雷《埃及宗教》)”通过“玛特”信仰,强调神的“至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解释权当然属于神职),故古埃及人的伦理核心就是维护“神”(国王)的绝对权威以及社会的既定秩序。因此,“妄图改变现状”是不被许可的。臣民若不听话,企图用破坏性激烈方式突破阶级的束缚,便会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面对人世间的苦难,只能沉默隐忍;或者贿赂神明(神职),以冀望于来世。这样,让所有现实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随风而逝。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说:埃及人“比任何民族都远为相信宗教。”我觉得不是埃及人迷信,而是祭司将宗教理论结合进了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同我国汉代时期的儒生(邹、董),用玄学联结“道”与现实,造成从上而下的自觉归化。(后出的《*帝内经》影响国人至今。)董氏有言:“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汉书·董仲舒传》)”谁不期待“天降祥瑞”呢?还是利用了人性中“趋吉避凶”的本能。
从古埃及的“冥神裁决”,到一神教的“末日审判”,还有我国民俗信仰中的“赏善罚恶”;一切宗教理论与行为之设计,都有其为某种目的服务的动机——这才更符合于古代原始信仰的真实状况。(河水涨落、日照长短自有道理和规律,与神明联结是积极宣传的结果;如此便能确立并树立起统治者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无论是上述举例的埃及法老,还是“黑暗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贵族,还有“轴心时代”的婆罗门;垄断了话语权的贵族集团利用神话对自身“授权”(乃至直接将上位者神格化),以证明其统治行为的正当性。虽然各民族与地区的文化表现与信仰模式都不相同,但“游戏规则”却没甚差异——一切源于人性的大同。
总之,“‘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活着治不了,死后算总账。或说因信得永生果,或说因善(依统治需要定义)得生天果;还有民俗技巧中的示好手段,以期在游戏规则中改写“参数”。有没有后门可以开?当然!既然“裁判”兼具人格,自然就好说话。最极端的说法是“神志决定论”——完全不问人为因素;即神权高于一切,一切归因于神——那这“因果”便是有“主宰”的因果。(最典型的案例是“约伯”。他原是一个有大福德的人,突然之间遭逢变故——天灾人祸令他失去儿女、家产、富有、健康,乃至一切。其后又大反转:最后约伯重新恢复往日的荣景。)但凡神教的“因果观”大抵如此。
在各类神教中,最具特色也最为圆融的是由雅利安人持续创造的婆罗门(印度)教。雅利安人原为乌拉尔山脉南部草原上的古老游牧民族;自北方南下,与三大古代原生文明接触,对彼此的文化既有干扰也有接纳。在中亚的一支经过总结与创造,形成拜火信仰。之后进入南亚次大陆的中部平原,对原住古达罗毗荼人的领地殖民统治,使社会阶级迅速分化。由于社会组织能力低下,除了武力以外只能仰赖信仰工具(吠陀)。垄断了传承知识的特权,教职阶级成为先天的“*金贵族”(婆罗门教)。婆罗门宣称:阶级天定、教职至上、向神示好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三大纲领”),遂逐渐成为*治、经济、司法、文化等诸领域的主宰者。
此外,“灵*不灭”、“业报不失”、“轮回不息”等思想也被继承下来,不断酝酿,发展出全新宗教形态(解脱追求);直接引发广大被统治者的“启蒙”。他们反对垄断、脱离世俗、简约生活、专注冥想、追求解脱(沙门)。这种“否定神权”、“人人平等”、“以人为本”的进步性,一度得到底层民众与刹帝利阶级的支持。(可惜“神”不眷顾所有人;再加上祭司喜欢*金,不如沙门只需一餐陋食,所以广大民众往往更倾向于后者。)与此同时,也刺激了婆罗门教更往“形上”领域发展(印度教)。对于千余年间辗转传来的各宗思想广泛参考,博采众长、后来居上,终成历史选择,传承至今;(得到人口便利,)成为世界第三大宗教。
与“种姓制度”类似的,是古代华夏文明的“宗法制度”;两者都是适应于农耕经济基础的社会良序。两种文明期初都是“神授治权”,统治集团是被“授权”与被“监督”的——这与古埃及不同。古埃及认为:法老王即神——这比“君权神授”多走了一步,便有天壤之别。因为神要面对人间现实苦难成因的问题;一旦失去权柄,即会引起需要耗费极大社会成本的变革。(所有神教都要面对的难题:人类的苦难到底是神赐予的?神未知的?还是神放任的?许多宗教都将问题推给“魔*”,甚至选择忽视。印度教接受邪恶的存在,不过把一切都视为表面的、虚假的、如幻的、不实的存在,便能够忍受比其他宗教更多的世俗痛苦。)
我国自“周公”起,“天子”概念形成,于是“神授”升级成为“天授”。“天”的“位格”趋于“形上”,(失去人格——部族属性,)这就有了突破阶级的可能。(《道德经》说:“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神不专属于哪一族人、哪一家人——人间没有永世不替的贵族。如《孟子·告子上》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天子”是“神”在人间的代表,故大家都是“天民”;只是分工不同、远近不同罢了。所以只有“化外之民”,没有“神”的敌人。化外之人是有教化可能的,不若种姓的先天决定,这是宗法制与种姓制度的根本区别。
“君权神授”模式在理论上可以由“问责罪己”与“革除天命”的方式实现“舆论监督”与权力汰换;至于“游戏规则”本身却不会遭到破坏。所以在此之后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也有战争,但大多是内部的对合法权的争取,不同于一族对另一族的殖民。华夏民族走到了时代的前列。社会被系统组织起来,一切都有标准(“礼乐”),人皆“敦伦尽分”。随着知识与门阀的垄断相继被早期儒家与科举制度打破,使得社会流通的压力得以释放。相反,印度神权社会的良序设计就不可能打破这一藩篱,所以才用发达的神学来消弭反抗心理。(尤其是印度教的“幻说”,令“善恶分别”成为世俗价值取向,而不再是宗教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