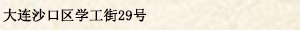汪正龙图像时代的文学变异文学与图像关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摘要新中国头三十年纸质文化和播放媒体(广播、收音机)占据主导地位。报纸、图书、广播是读者阅读或信息获取的主渠道。新时期以来,随着电视、电脑、手机的普及以及电影的产业化改革,我国进入了图像时代。图像时代的到来催生了新的文学类型,也改变了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图像摆脱了对叙事的依附地位,出现了越来越多文图合一的复合文本,它们追求可知性与可视性的对等性;特别是一些自媒体视频挣脱语言、文字甚至声音的束缚,展现了独立叙事的可能性。表面上看,上述趋势体现了语言的保守性和图像的活跃性,其实是欲望与图像及观看之间默契关系的表现。
关键词图像;文学;文图关系;独立叙事
作者汪正龙,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年第10期。
目录
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和文学与图像关系的改变
二、文图合一的复合型文本:可知性与可视性之间的对等性?
三、自媒体视频与图像独立叙事的可能性
图像时代的文学变异
——文学与图像关系的演变及其理论思考
新中国头三十年纸质文化和播放媒体占据主导地位。报纸、图书、广播、收音机是读者阅读或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虽然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于年开播,但是电视的普及还是三十年之后的事情。电影由于出品量比较少——据不完全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年累计发行长短影片部,“文革”时期仅为36部,加之放映单位和放映场次有限,也没有成为大众的主要文化活动方式。自年改革开放至今,媒体或媒介的演变经历了纸质图书、报刊、广播、收音机、电视、电脑、手机等多个阶段。特别是随着电视、电脑、手机的普及,数字媒体已经取代了纸质媒体与播放媒体,占据了主导地位。电视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百姓家庭,90年代全面普及。年6月,中国网民达到2.53亿人,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到了年,智能电视的普及率已经达到84.5%,手机用户达到12.86亿户,普及率为94.5部∕百人,中国网民人数达到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城市个人电脑普及率也超过80%。到了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8.29亿,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电影在新时期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自年走向产业化改革,实行“院线制”以来,无论从出品数量,还是从银幕数、观影人数、票房收入看,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大国。动态地看,中国可以说既算是进入“新媒体”时代,即计算机网络和数字媒体时代,也是“全媒体”时代,即纸质媒体、播放媒体与数字媒体并存共生、交叉互动的时代。人们的阅读方式和信息摄取方式也经历了从纸质媒体到数字媒介,从报纸、广播到影视、电脑、手机等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开始用“图像时代”来命名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图像时代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面貌,包括创作、传播和阅读方式等。本文拟就此做一番考察,并对由此引发的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
和文学与图像关系的改变
海德格尔曾经把图像化视为现代性的标志之一。他说:“从本质上说,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标志着现代的本质。”斯洛文尼亚美学家阿莱斯·艾尔雅维茨也说:“在艺术和文化领域的‘视觉的’和‘图像的’转向问题(正如理查德·罗蒂早些年所描述的,这种艺术和文化的‘视觉的’和‘图像的’转向与‘语言学’转向是对立的)是哲学和社会理论中展开的众多讨论和出版物的主题。”艾尔雅维茨所说的“视觉转向”或“图像转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生态,构建了新型的文学与图像关系。
首先,视觉转向与图像转向改变了先前纸质文学的存在形态,其中有两件事 有代表性:一是连环画在经历了新时期初期的短暂辉煌之后,被后来居上的漫画书所取代;二是插图本文学特别是插图本小说语言与图像的关系发生改变。先来说连环画。20世纪30年代、50-60年代,连环画曾经有过两次繁荣期,特别是第二个繁荣期,以红色经典为基本创作素材的连环画被称为“解放书”广泛发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不仅涌现了刘继卣、贺友直等大师级画家,还于年举行了首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不过,连环画虽然在新时期迎来了它 繁荣期,但是在年达到峰值后逐步走向衰落,“年出版种,8.67亿册,平均每种39.99万册。此后的两年中,连环画的发行量均达到了较高水平。年出版种,发行8.16亿册,平均每种27万册,可谓形势喜人。……年品种跌至种,印行册数跌至1.33亿册,平均每种6.68万册,年跌至种,印行0.79亿册,平均每种6.37万册。以年和年相比,年的品种、册数和平均每种册数各为年的41.35%、9.68%和23.59%,品种减少了58.65%,而册数锐减了90.32%”,“至年,连环画出版品种已经下降到种左右,几百万册”。年后全国范围内基本上不再出版连环画。
从表面上看,连环画的衰落除了电视的普及和读者、大众娱乐休闲方式的多样化之外,漫画书的冲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开始引进日本漫画书。自年引入龙珠漫画《小猴王》之后,这股思潮一发不可收,手冢治虫的《铁臂阿童木》、井上雄彦的《灌篮高手》、尾田荣一郎的《海贼王》、藤子·F.不二雄的《哆啦A梦》等日本 漫画书在我国风靡一时。我国90年代以来本土漫画书逐步兴起,21世纪以来其影响也日益扩大,代表作有朱斌的《爆笑校园》、周洪滨等的《偷星九月天》、颜开的《星海镖师》、夏达的《子不语》、口袋巧克力的《昨日青空》等等。但是深究起来,漫画书之所以能取代连环画,是因为连环画仍然带有比较浓厚的传统叙事的痕迹:遵循“脚本先行”的创作原则,以文字叙事为主,图像成为语言的附庸;漫画书则是以夸张、变形、特写的图像为主,语言穿插在图像之中,追求故事的紧凑呈现,其造型勾勒和人物转换借鉴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读者在“翻阅”中享受阅读的快乐。也就是说,漫画书的兴起带有鲜明的图像时代的特征。然就总体状况而言,国产漫画书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在构思和技术上还带有日本漫画书影响的明显痕迹。例如,近年来国外主要针对成年人的图像小说(graphicnovel)很火爆。图像小说集漫画与小说为一体,试图将断续的图像转化为连续的情节。但是这类创作在国内基本上还没有什么人去尝试,甚至由法国作家马蒂与中国画家聂崇瑞合作创作、在法国热销的《包拯传奇》,引进国内后也没有引起相应的反响。可见,中国的漫画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再来看插图本小说,一个重大变化是图像在小说创作中的比重与地位显著上升。本来,小说插图通常只是对正文起补充作用,近来则成为小说的有机构成,超越了先前文学插图的附属性与装饰性。例如金宇澄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繁花》,正文中嵌入作者手绘的二十幅插图,有皋兰路屋顶、国泰电影院、瑞金路长乐路的变迁、卢湾区地图、沪西地图、上海中心城区地图等,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图画具有独立的审美内涵并融入正文的叙述链条之中,保留了已经消逝的老上海记忆,成为个性化的城市景观有意味的再现。如第十一章“历史城市初稿”这幅插图本身就是三图并置的,勾勒出长乐路一个街角四十年的变迁。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中这二十幅插图并不依附于叙事,因为它们与正文故事的关系并无对应关系,有的在正文叙述部分之前,有的在正文叙述部分之后,起到了类似“记忆”或影视“回放”的效果,具有某种独立叙事功能。文学史上作者为自己作品作插图的情况并不鲜见,萨克雷曾经为《名利场》插图,鲁迅也曾为《阿Q正传》插图,但是像金宇澄《繁花》这样使插图与正文形成对话甚至复调效果的还比较少见。
《繁花》插图:历史城市初稿(图片来自百度)
其次,新兴媒体的出现,催生了新的文学类型,如网络文学、手机短信文学、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等等应运而生,形成了新的文图关系。新兴的网络文学不仅引入了图像因素,网络文学的虚拟性和互动性也改变了传统文学以作者为中心的单向线性发展模式,具有视觉图画性。例如署名“家是我的一切”所著的网络小说《出轨了离婚了不要脸了,婆婆你满意了吗?》就是如此:
楼主:家是我的一切发表时间-11-7
国庆假期的喜庆还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而我即将要去办离婚手续了,离婚的直接原因是我的出轨。……我承认在婚姻的道路上,没有忠于自己的选择,没做到忠于丈夫,一个完整的家面临着破碎,我自己也成了传统意识中那种无耻、不要脸的女人。我恨自己走错一步葬送了一个好好的家,更恨我的婆婆。
一楼网友发表时间-11-7
先不要忙着批判自己,我相信事出必有因,有因必有果。
楼主:家是我的一切发表时间-11-7
刚知道我的时候,你说我是家里的不祥之兆,会方死人。流产卧床的时候,你说我靠怀孕骗婚,是光叫不下蛋的鸡。生了儿子,你让我离孩子远点儿,因为我不懂怎么养育孩子。 当着你儿子的面一个耳光打在我脸上,怒斥老公“你护着她就没我这个妈”……
从上述写作模式看,这篇小说可以说是楼主和网友共同创作的,具有开放性和未完成性,也开拓了文学与图像关系的新领域。楼主发帖,网友跟帖,楼主根据网友的意见不断调整故事进程甚至自己的写作状态。这样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参与不仅构成了复合型文本,还使得文本的呈现方式具有类似于多种声音对话式展开的戏剧性,以及楼主、网友互动的具象的图画性。
可见,从文学与图像关系演变在文学文本中的体现来看,新时期文学已经从传统静态的插图本文学“以文为主,以图释文”的文学存在方式,走向文学与自主图像及动态图像相结合,包括漫画书、文学的影视改编、MTV、新媒体写作、网络游戏与自媒体视频等等,其中的图像越来越具有某种自主性。在某些自媒体网络视频中,图像甚至摆脱了语言文字甚至声音的制约,走向独立叙事。可以说,从静态图像为主转向以动态图像为主,是新时期文学与图像关系的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文字符号的功能在弱化,慢慢走向声画合一,在影视改编、MTV和网络视频中,语言、声音、图像或并置或汇拢形成意义增殖。也就是说,图像与语言一样,具有某种施为性,从而形成了意义的叠加效应。
二、文图合一的复合型文本:
可知性与可视性之间的对等性?
米歇尔说过,我们需要研究“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这种再现: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没有‘纯粹的’视觉或语言艺术”。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在我国新时期表现得十分显著。面对视觉转向与图像转向,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改变了生存策略,以新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与图像相结合,构筑文图合一的复合文本。大致而言,这种结合与互动有以下四种形态:
一是文学和影视相结合。除了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之外,不少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名著如《围城》《四世同堂》《红高粱》等也被改编成电视剧,不少作家更是热衷于编撰影视剧本,通过影视改编而走红。影视向文学借鉴,文学对影视依附。例如,张艺谋本人执导的二十多部影片,其中近八成改编自文学作品。这种情况愈演愈烈。近来把网络文学改编成影视剧渐成风气,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甄嬛传》《琅琊榜》《花千骨》《芈月传》等即为例证,《*吹灯》改编的电影《寻龙诀》《九层妖塔》也很受欢迎。甚至还产生了《暗算》这类的“电视小说”,即先通过影像的传播,反过来促成与扩大小说的传播。
二是文学与摄影相结合。从年起,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冯克力主编的“老照片”系列丛书,以老照片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同类著作还有郑佳明主编的《长沙百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年),书中收录了一个半世纪以来长沙城的幅照片。这类作品集纪实性与观赏性于一体。还有不少散文、传记、游记类作品,也有大量摄影配图,例如叶兆言《老南京:旧影秦淮》(江苏美术出版社年)、杨绛《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钱德文《风雅秦淮》(南京出版社年)、叶永烈《傅雷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年)、姜建、王庆华《朱自清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年)、郭平《巴厘巴厘——一个中国人的30次巴厘岛之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等。这类作品中还有部分把文学与摄影、绘画、书法相结合,主要是游记或考察记,如冯骥才《凝视达·芬奇——意大利名画亲历记》(译林出版社年)、俞剑华《敦煌艺术考察记》(东南大学出版社年)等。前者讲述了冯骥才赴意大利各博物馆、美术馆观赏名画的经历,配有这些名画的图片,也附有作者考察时沿途所拍的照片或参观时的影像资料;后者则以影印的方式展示了俞剑华游历敦煌的手写书法、绘画作品。这些作品的特点是照片充当历史或风物的见证,与文字记述的历史、人物及景观构成互文关系。学者金宏宇指出现代文学图像至少有四种价值,即欣赏价值、商业价值、阐释价值与历史价值,其中有些文学图像还“有一种文字所不及的直接象征暗示作用,可以表达更精微、不易察觉、可心悟而不可逻辑论证的某些精神意蕴,可以与文学作品构成一种特殊的阐释关系——互文性阐释。”显然,不仅是插图,摄影同样也可以起到这种作用。
《我们仨》
在文学与摄影相结合的作品中,杨绛的散文《我们仨》特别有代表性。该书实际上把文字、照片、绘画、钢笔书法熔为一炉,构筑了多层面的复合文本。
《我们仨》这部作品的特别之处在于,正文由“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三部分构成,但是正文之前和当中穿插了钱锺书的手迹、钱锺书、杨绛夫妇以及他俩和女儿钱瑗的大量照片,正文后面占全书四分之一篇幅是钱瑗的手迹,包括书信、回忆手稿、给钱锺书的画像等,既构筑了叙述张力,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梅洛-庞蒂曾经这样评价塞尚的绘画:“塞尚的天才之处在于,通过画面的整体安排,让那些透视变形在统观画面的人眼中就它们自身而言不再可见,并让它们就像在自然视觉中所做的那样,仅仅有助于提供的印象是一种诞生中的秩序,正在我们眼前显现、堆积的一个物体。”我们可以把梅洛-庞蒂评价塞尚绘画的话套用到杨绛这部作品上,由文字、照片、手迹整合的这部作品恰好完美地体现了妻子、丈夫、女儿——“我(杨绛)”、钱锺书(你)、钱瑗(她)“诞生中的秩序”,不仅没有嵌合、拼贴的痕迹,也与他们三个人发生关联的空间与顺序相契合。
钱锺书夫妇照片及钱瑗给钱锺书的画像(图片来自百度)
三是文学和网络相结合,形成新媒体文学(数字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等。中国大陆的网络文学兴起于90年代末,早期作品如罗森的《风姿物语》受到日本动漫和西方奇幻文学的影响,年后随着起点中文网、晋江原创网、小说阅读网等网站的陆续创办,线下的创作进入线上,网络作家通过网站积聚、交流,网络文学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玄幻、穿越、宫斗、言情、科幻……新的题材与创意络绎不绝。近年来,现实题材的作品表现强劲,出现了《我不是药神》《大江东去》等作品,以此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剧也受到一致的好评。先前的纸质型写作创作过程与传播、阅读过程是分离的,现在的电子超文本文学创作则追求文图互动甚至多重链接,虚拟性和交互性是电子超文本写作的重要特征。特别是网络游戏,代入感很强,玩家充当游戏的主角,在一步步晋级中欲罢不能,体验成功的快感。实际上,网络文学与网络游戏几乎是共生的,好的网络文学往往被改编成网络游戏。比如像唐家三少这样的大神级网络文学作家,不仅擅长线上、线下同步创作,即网文连载和图书出版同期完成,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