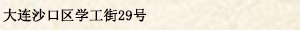舌尖上的枝江
之一:舌尖上的枝江之地方特色菜
说菜之前,先说说作料。
现在饭店里五花八门的作料,在咱们枝江使用,其实没多长的历史。家庭主妇们使用得最多的,还是具有本地特色的作料,最主要的是三大样:豆豉、盐菜、鲊海椒。这些作料,单独作为佐餐小菜,也挺不错。
先说豆豉。这豆豉不是那个豆豉,四川叫做豆瓣酱。这是枝江的作料 ,应用广泛,几乎可以用于所有菜的制作。无论哪家,每年夏天都得做,少则一坛,多则两三坛。制作倒也简单,把红辣椒去蒂洗净,剁碎,加上拍碎的大蒜、花椒、生姜、八角、桂皮和适量的盐,把沤好的蚕豆瓣(我们叫豌豆瓣子)淘洗干净(也有的人说只需把其中的灰土去掉就行,不能淘得太干净,把那个*色的霉灰弄没了,豆豉就没那么好的味道了),和剁碎的辣椒搅拌均匀,装坛密封,过个个把星期就好了。
盐菜,有地方也叫腌菜。把青菜或者大头菜的菜叶洗净,加上盐放在大缸等容器里,用洗净的大石头压上,夸张的甚至用磨盘压。几天后菜叶变色,沁出的菜汁淹没了菜,就可以出缸了,晾晒干后,装入葡坛,就是那种口朝下的坛子,压紧,塞上洗净的稻草把子,口朝下放在装水的浅子里。
鲊海椒则是把米面或者玉米面和剁碎的辣椒搅拌均匀,也像盐菜那样放进葡坛里。讲究些的还在稻草下面加一张荷叶,免得鲊海椒里面掺杂了稻草碎屑。鲊海椒越炕颜色越深,味道就越好。
还有一种是稀辣酱,先期做法和豆豉差不多,只是不加豆瓣,然后用石磨磨成酱,现在一般是机器打的了。这东西刚磨出来时,用来拌饭吃非常好吃!
枝江的本地菜,没有了这几样作料,那就没有那个味了,所以,漂泊在外的枝江人,都十分怀念这些东西。一个朋友的弟弟,当兵外出,后落户沈阳,官儿还做得不小,每日山珍海味吃腻味了,就是想念这些东西,于是就叫在家的大哥给他寄,每年两次,每次邮费都得百十来块。有的有机会回来,就用装食用油的大壶装上一壶豆豉带上,也可以吃上个把月,盖子拧紧了也不会变坏。
罗嗦了半天,该说菜了。
先说一个时令酒菜:新鲜菜油拌豌豆。现在,新菜油刚榨出来,花椒也成熟了,正是吃这个菜的时候。把新鲜豌豆炒熟,放进冷水里,过一会,待豌豆变软后沥干,倒入生菜油,注意,一定是生菜油,再加上拍碎的新花椒、盐。豆豉水,搅拌均匀即可。 次吃,会因为生菜油的那个味儿而不习惯,但你只要就着豌豆喝完了这顿酒,你就再也不会忘记它的那种独特的味道了。在一些 酒友中有一句话,叫“豌豆喝酒——确!”可见其佐酒之妙。
烘藕。这个“烘”,在枝江话中还有“煮”的意思。春节时,这是七星台一带每家必备的。把藕切大块,和猪蹄、鸡子等放在大锅里慢慢烘,不能用铁锅,那样容易变黑。煮好后,汤如米汤一般呈乳白色,闻上去有腊肉的香味、藕的清香,尝一口,还有一丝甜味。藕进口即碎,面噜噜的。那些年过年期间,虽说我整天流连于酒桌之上,但是肚子里却永远是空空的,每当饿得不行了,就拿一大海碗盛上一碗饭,倒上藕汤,呼啦啦吃下去才保住了小命。不过这种美味已即将成为回忆了,因为没有那样的藕了。枝江的藕大致分为两种:白莲藕和柴藕。白莲藕用于爆炒,清脆爽口:柴藕用于熬汤,汤鲜藕面。而现在,泛滥成灾的是产量高的杂交藕,炒着吃吧,它是绵的,烘了吃吧,又烘不趴(不知道这个字怎样写,软的意思)。
腊肉盐菜炖鳝鱼。枝江盛产鳝鱼,做法多样,盐菜炖鳝鱼算是其中的代表了。要大点的鳝鱼,大拇指粗细 。
杀鳝鱼也是个技术活,不会的人弄半天还炒不到一盘。你可以把菜刀的一个角磨得非常锋利,然后找一块砖头或者找一个坎,把刀踩在脚下,磨锋利的那个刀角朝外,右手掐住鳝鱼,将鳝鱼的头朝地下猛击,然后右手捏住已被打碎的鳝鱼头,肚皮朝向刀角,左手轻捏着鳝鱼身子放在刀角位置,先向刀角用力,使刀角刺进鳝鱼肚皮,左手稳住不动,右手向右拉去,鳝鱼就被剖开了。拉出鱼肠后, 是把鳝鱼锤一下,把鳝鱼背朝上放在木板上,再用木块等锤鳝鱼,锤好的鳝鱼是摊开的,卷着。锤的目的是将其骨头脆碎,使骨头中的物质更容易出来,味道更好。顺便说一下,做这事儿时 穿上罩衣,以免弄得浑身是血。
将杀好的鳝鱼先切成段,然后将腊肉熬油,放进鳝鱼爆炒,加上作料,加入盐菜,多放点辣子,放入足够多的水,然后就慢慢地炖。炖好后,鳝鱼好吃,盐菜好吃,汤也好喝。
鳝鱼的另一种做法是炒盘鳝。这种做法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起来的,记得 次吃盘蟮时,一桌人没一个会吃,把厨房的师傅叫出来请教,他说他只会做不会吃,于是一桌人都一手抓头一手抓尾,像啃包谷那样吃,弄得满手满脸都是,太累人了。到后来才摸索出来,用筷子夹住鳝鱼头,用门牙轻轻咬断鳝鱼脊骨,再轻轻一拉就行了,这是后话。
做盘蟮得选那些筷子粗细的鳝鱼。大了盘不拢,小了吃不上嘴。这种做法有些残忍,鳝鱼是活生生被烫死的,所以,鳝鱼刚下锅的时候,必须用锅盖盖着锅,不然鳝鱼就都跳出锅去了。鳝鱼死后,加入豆豉、姜末、辣子等作料,慢慢翻炒,待鳝鱼都卷成如蚊香一样的卷时就成了。因为是活的下锅,鲜就不用说了,肉嫩,骨脆,滋味好。就连豆豉姜末作料等吃起来也妙不可言,用于下饭再好也没有。
ps:这篇文章是春末夏初的时候写的,所以文中就把那个新鲜菜油拌豌豆说成了时令酒菜。
之二:舌尖上的枝江之地方特色菜
炖菌子。这个菌子特指本地的茅草菌,不是那些人工培育的那个菇这个菇。茅草菌最常见的是松菌,呈谈红色。人们说 吃的是所谓的“扣子菌子”,就是个头如扣子般大小,实际不然,扣子菌子口感虽好,但是味道不是上乘, 的是那种个头如旧时银元大小,也就是成年人拇指食指相扣大小的菌子。再大一些,菌子的边缘出现裂缝时,那就老了。松菌长得很快,一般两天左右就老了,这种菌子,一老就不好吃了,嚼在口里如木渣一般。
比松菌好的是乌菌。呈乌灰色,肉头比松菌厚,味道也比松菌好很多,但是数量少。
的是鸡爪菌,白色,摸样有点像金针菇,一簇一簇的,又像盛开的菊花。这种菌子味道非常鲜美,但是数量极少,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我这辈子只在小时候吃过两次,都是在屋后的竹园里寻到的。
茅草菌的生长需要适宜的温度、湿度,时间是夏末秋初,只在下雨后晴一两天后,才能在茅草山上找到。
菌子好吃,但它非得动物油不行,植物油放的再多,也不是那个味儿,吃多了也刮人。用排骨或者土鸡炖上,肉香和菌子香相得益彰,汤尤其鲜美,令人难忘。
还可以把油烧开,把菌子放在油里略炸一下,然后将菌子和油盛在一起密封,做成菌子油。吃面条或者做凉拌菜的时候放上一点,味道也很鲜。
炖地钱皮。不知道学名叫什么,像黑木耳一样。夏秋季,雨下的时间长一些,就可以拣得到。以前的匹匹很大,和发开的木耳相似,但是现在好像个头都很小了,只有指甲盖大小了。把几个青椒一切两半,和地钱皮一起爆炒,然后炖上, 加上点生鲊海椒,味道独特,很不错。但是这东西没什么营养。
说两个小菜,做法简单,但是好吃。
蒸茄子。将茄子去蒂洗净,整个撒上点盐,放在蒸锅上蒸,也可以在蒸饭的时候放上蒸屉蒸。蒸熟后放凉,用水冲一下,再撕成一条一条的,拌上豆豉水、酱油、香油就成了,甜辣咸香,佐酒最妙。
揉芫荽菜。将嫩芫荽洗净,拧成两段,放在大碗里,用手揉出汁,加上适量的盐就行了,什么都别放,包括油,就吃那个原汁原味。估计对减肥有效果。
这些都是家常菜,餐馆里诸味齐备的大菜,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之三:舌尖上的枝江之主食篇
其实,枝江所谓的主食,就只有一种:米饭。其他的,都统统称之为“杂粮”。
说到米饭,就得说一句本地俗话:“好吃不过甑子饭”。现在,无论城乡,煮饭大概都是用电饭锅吧,撇脱啊。但是电饭锅煮出来的饭只能说是饭罢了,不,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饭”,顶多是“闷巴坨”。它不是一粒一粒的,而是一坨坨,好吃根本谈不上。
甑子饭就不同了。现在农村家里过事,还是总要安排一个人专司做饭,做的就是甑子饭。有些家里还有甑子的,三十那天,是一定要做一甑子饭的。
做甑子饭是要一定的技术的,搞不好它就是不来汽,饭也就蒸不熟。相传这是因为得罪了先人所致,你得在灶口给先人烧纸,先人才会让你的饭熟。但我见过你别说烧纸,就是磕头它就是不熟的情况。
做甑子饭,先把米放在锅里煮,刚一断生,就要沥饭。然后把甑子的格子上铺上布,把沥好的饭倒进甑子,再密封好,锅里放上适量的水,大火猛蒸。那种不来汽的情况大多是沥饭迟了,饭粒容易粘在一起,不易透气,所以不好蒸熟。
甑子一般都是杉木或者松木所做,所以蒸出来的饭有一股清香,饭也是一粒一粒的,晶莹剔透,吃在口里,口感非常好。
当然,大米做出来的最香的食物,还得数锅巴稀饭。香!太香了!
做出好的锅巴稀饭,讲究的是一个火候。也是先沥饭。不爱吃硬饭的,可以适当多煮一会。沥好后,米汤放着。再把沥好的饭放进锅里,围上水,用文火慢慢蒸,你如果是烧的劈柴之类的硬柴,就不用再加火,时不时去灶里扒拉一下就行。这就要注意火候了,火小了,锅巴没有糊,稀饭就不香,火大了,锅巴糊大发了,那也难吃。饭熟后,盛出饭留下锅巴,灶里加火,然后把米汤倒进去,搅和一下,多煮一会就成了。盛一碗,焦香扑鼻,吃一口,回味悠长。我只要有锅巴稀饭,不吃的撑着是不放碗的。
苕稀饭也很好吃。那些年粮食紧张的时候,苕就是几个月的口粮,但是光吃苕不好吃,也不当饿,所以一般是把苕夹着米一起做成苕饭。现在吃苕是换口味,觉得很香。儿子还小的时候,我给他忆苦思甜,说你老子小时光吃苕饭了,想吃一顿光米饭都是奢望,哪想这小子一脸羡慕的表情,说,您小时候天天有苕吃?咋这么幸福呢?我哭笑不得,没有话说。实际上苕饭不好吃,但是苕稀饭却很好吃,米香加上苕的甜味,真乃美味。苕稀饭也可单独做,把苕切成丁, 是和糯米一起小火慢熬,香香的,糯糯的,甜甜的。
至于面粉,包谷之类的杂粮,因为不是主食,做法也很单调,乏善可陈,不再多说。
之四:舌尖上的枝江之水果篇
一部《舌尖上的中国》,令天下的饕餮之徒口水长流,也勾起了我的回忆。
小时候家里穷啊,哪里来钱让我们买零食解馋哪。但是嘴馋是孩子的天性,为了解馋,只好到大自然中去寻找了。
先得说一个我们当地的奇人,高老。高老姓邬,大号邬佑高,长相奇特。右额上长有鸡蛋大一个包,明晃晃的,在小孩子看来,十分可怕。后来看《射雕英雄传》,里面有个头上长包的侯通海,脑海里面立即闪现出高老的形象,这是题外话。高老是我们那群小孩子又恨又怕的人,但也是我们最想讨好的人。原因就在于他家里栽满了奇花异果,十分诱人。他家有四棵当时非常少见的栀子花树,每棵都有坟头大小,每到初夏,树上开满了栀子花,真有“千朵万朵压枝低”的感觉,香气浓郁。当然这些花花朵朵对我们这些男孩子是没多大吸引力的,最吸引我们的,是他家里的那些我们当地从没见过的奇异水果。
就说桃子。平时见到的,多是一些狗屎桃子,长不大(也许是从来没机会长大,桃子上还满是毛,核还没长硬的时候就被我们给摘光了),少数家里有一两棵白桃,那也让主人看得紧紧地,捞不着。高老家里的桃子,有大白桃,比一般的大多了,还有扁桃!扁桃又叫磨儿桃,现在也有,但是,高老家里的大多了,甜多了,当时可是绝无仅有的,除此一家,别无分店。
他家还有两颗柿子树。这也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大小有小孩儿拳头大,没等熟透,高老就摘下来了。我们也曾去偷过一些,迫不及待的咬一口,却是涩得张不开嘴。听别人说,要把狮子放在米缸里捂一段时间,待狮子变软后才好吃。但是我们战战兢兢偷不了几个,在米缸里过不了两天就刨一个出来尝尝,还没等柿子变软早就没了,所以我从未吃过传说中又甜又香的柿子。
还有一些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高老夸口言道,他家除了没有樱桃树,什么树都有。幼时的我深以为然,甚至还曾天真的想过,要是我爹妈把我送给高老就好了。
要弄到高老的水果,正常渠道是很难的,所以还得到野外去寻。
吃的,莫过于栽秧果子,到现在我还依然认为,栽秧果子是我吃过的 的水果!栽秧果子一般长在水田的高坎上,有点像草莓。果实是一个托上排列着如高粱般大小的晶莹剔透、红得透亮的果粒,非常甜,微酸,十分爽口。但是这东西数量不多,要吃到它,那是可遇不可求的。奇怪的是,每每我发现的都是未成熟的,即便有时发现有成熟的,那也只有一颗两颗,根本不能解馋。
另一种好吃的,是老杨家的米枣子。这种枣子,个头不大,但很甜。杨家的枣树在他家门前稻场的堰边,本来爬树对于我们来说不是难事,但是枣树就在人家门前,也不能明目张胆去摘。于是我们就利用在水里玩水的时候,趁人家不注意,摸起石头住上砸,掉在水里的,就是我们的胜利果实了。枣子将要成熟的时候,我们这一群半大小子,就整天泡在那口堰里。
好吃的东西总是不多,于是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凡是能吃的,都弄来尝尝。吃过蛇果子,就是野生草莓,老人说,它被蛇爬过,吃了会死人的。我们就把蛇果子表面那层红皮扒掉,吃里面的白白的果肉,样子很诱人,除了水分足,实际上没什么滋味。吃过嫩包谷秸秆,有点甜味,比甘蔗差远了。还吃过一种不知名的野草果,像个小灯笼,里面有一颗像木碗子的浆果,青的时候很酸,变*了,就有些甜味了。春天没果子可吃,就把野蔷薇的嫩茎折来,剥了皮吃,有一点清甜。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水果可谓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但是,我却从来没有过儿时的那种美味感觉了。
之五:舌尖上的枝江之零食篇
现在说起零食,大家首先想起来的肯定是超市、小卖店,那里的零食琳琅满目,诸味齐备,站在那里不动,吃上个半天都不带重样的。不过在几十年前,馋嘴的孩子们想要弄点什么零食解解馋,那还真不是什么简单事儿。为什么?穷啊。
还是说说我的记忆吧。小时候,大队里也开办了代销点。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代销点。那时候,除了国营和集体经营,不允许个体开店子,为方便群众,个别离集市较远的地方,就可以办一个代销点,所有的货物都是供销社提供,过一段时间就要清铺,也就是核对款物能不能对得上。我们大队开办的代销点,是一个姓刘的裁缝主事的。现在想起来,那时这个代销点对我 的诱惑就是“堆烧饼子”了。所谓的“堆烧饼子”,大小如鸭蛋,扁平状,每十个堆起来,用纸包扎起来,每包是一毛还是一毛二我忘了,用两个鸡蛋可以换一包。那东西又甜又酥又脆,太好吃了! 美中不足的是,容易钻腮,吃过一个,两边牙缝里都塞满了。但是你想想,那个时候,家里的每个鸡蛋父母都有数的情况下,要弄个角把两角钱,那是多么的不容易!
那时候,自家出产的零食有限,粮食不够哇。我自认为最美味的就数苕米子,也叫苕筋果。我们那一带出产红苕,将红苕切片,讲究些的切成条状,然后煮熟,捞出沥干,再放在帘子上晒干。晒到半干的时候,苕米子很甜,就是太粘牙了,牙齿不好的人难得吃下去。待干透后,一般在腊月间,就用沙子将苕米子炒熟,炒熟后的苕米子,焦*酥脆,甜香可口。这东西也不是敞开了吃的,得留着过年时待客。现在也有,但是已经不是用沙子炒了,用沙子炒,容易带上沙子,硌牙。现在都用盐来炒了,用作下酒不错。
再一种就是炒豌豆。方法和炒苕米子差不多,都是用沙子把豌豆放在锅里翻炒,等豌豆炸开口子的时候就行了。这也一般是过年的时候才能想得着。
打巴糖。据说用红苕熬制,方法不详。一般家户人家不做这个,都是小贩挑着买的。一担箩筐或者箢子,里面放着大块的打巴糖,有人叫买,就用小锤子在大块上敲下适量。大巴糖很甜很香,但就是非常粘牙,一小块打巴糖吃下来,牙巴骨酸得很。
穿穿子。用面粉擀成面皮,和面的时候加上糖,不过那时候一般是加上糖精,糖太贵了。把面皮切成长方形,然后在上面纵向或者横向划上两刀,不要切断,再把两端从切开的口子里绕过去,放在滚油里炸脆。这东西制作很复杂,但实际上并不好吃,我以为。
麻花子。它的制作需要一定的技术,家户人家也很少有自己做的。相传,当年枝江的几大特产之一,就是屈家店子的麻花子。据说,屈家店子的麻花子,只能用当地一口堰里的而且只能是一个埠头里的水才能做出来,那麻花子,酥脆爽口,入口即化。别的地方一盒麻花子十个,屈家店子的麻花是一盒二十个。我也吃过,的确比其它地方的麻花好多了。只是不知道现在屈家店子的麻花还有没有。
之六:舌尖上的枝江之鲊海椒
鲊海椒是我们枝江很常见的“陈菜”,制作方法前面已说过,此不赘述。那些年生活困难的时候,这几乎是每个家庭尤其是家有学生家庭必备的,它一经炕熟,就不易变质,很适合住校学生。就是平常家庭,也是个配菜,用家庭主妇的话来说,可以让客人筷子有个转弯的地方。春节期间,由于香肠啊,猪肝啊、耳朵啊这些菜太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一切就是几节,而是薄薄的切上几片,在碗底装上一大碗鲊海椒,再把上面弄得圆圆的,然后铺上一层。好看一些。这都是往事了,现在的孩子们很难理解。
现在鲊海椒已经成了一道不错的地方菜了。
鲊海椒炒肥肠。很多餐馆里都有这道菜,下饭 。舀几勺子鲊海椒,和饭一拌,吃得大汗淋漓,喝酒后吃的最痛快了。
鲊海椒糊涂。前文说过,鲊海椒几乎是全能调料,在吃火锅后,用火锅汤,加上几勺鲊海椒,就成了鲊海椒糊涂,非常美味!很多人是用已经炕熟的鲊海椒,实际上用生鲊海椒更好。但是要注意的是,鲊海椒加入锅里后容易巴锅,所以要不时搅和一下。
鲊海椒煎鸡蛋。把鸡蛋打入鲊海椒,搅拌均匀,锅里放油,煎熟即可。黑色的鲊海椒夹杂着*色的鸡蛋,看上去很美,吃上去更美。
之七:舌尖上的枝江之米豆腐
豆腐,是中国人都知道。但是我们枝江还有一种豆腐:米豆腐。如果严格按照豆腐的定义,这应该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豆腐,因为它是用大米制作而成的。
很惭愧,我现在对米豆腐的制作流程已不是那么清楚了,尽管还是经常吃它。留存的印象是,把大米用石灰水浸泡至软,然后加上辣酱、盐,磨成米浆,然后煮熟,出锅,等凉了后,就凝结成豆腐般的样子。
米豆腐是一种味道独特的菜肴。我一个年长的同事,每到餐馆吃饭,必点米豆腐,而且是两盘。它有一种其它菜肴没有的石灰辛辣味,再加上辣酱带来的辣味,佐酒下饭俱妙。
一种做法是煎。把米豆腐切成不厚不薄的片,锅里放足够的油,将米豆腐片放入锅内,煎成二面焦*,出锅就行。另一种是把米豆腐切成条状,晾干,然后油炸。此种做法佐酒最妙。还有一种是用来下火锅,但是容易巴锅,并不是 的吃法,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舌尖上的枝江之八:当下的时令小菜
时值春末夏初,本是蔬菜淡季,但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些味道独特的小菜。
野韭菜煎鸡蛋。说是野韭菜,但是和韭菜一点也不像,倒有点像葱。生长在旱田里,一丛一丛的,香气浓郁。扯上一把,摘净切碎,打上鸡蛋,煎熟,闻起来很香,但是吃起来味道一般。不过春天到了,这也算是应个景。
椿天树芽子煎鸡蛋。椿天树,就是椿树。仲春时节,椿天树萌发新叶了,呈紫红色,有一种很独特的味道。把嫩叶掰下来,洗净切碎,煎鸡蛋也不错。但是很多人忍受不了那种独特的味道而不爱吃。
炖臭豆腐渣。年前做年豆腐的时候,把豆腐渣炕熟,找个坛子装进去,压紧,过年后温度上来就臭了,臭豆腐渣由原来的颗粒状变得粘在一起了,一打开坛子,臭气熏天。但是这东西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先把油白菜或者白菜苔或者牛皮菜(也有叫甜菜、丁达菜)梗子用猪油炒熟,多加辣子,然后加上一两勺子臭豆腐渣,炖烂。那叫一个好吃!今年春节一伙朋友到家来,老婆炖了一大锅,大家伙儿一人一碗,一会就空了。
作者:夏侯婴(来自天涯论坛)
北京哪个医院白癜风治疗 白癜风怎么治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