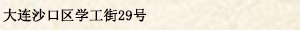刺客聂隐娘一段传奇下
四、聂锋之死
故事接着往下说:
▌数年后,父卒。魏帅稍知其异,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如此又数年。
这段话乍一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可如果翻看一下『聂隐娘』故事主体所在的时间线,也就是德宗贞元年间到宪宗元和年间,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魏博节度使前后有过四任:兴元元年()叛乱夺位的田绪,贞元十二年()继任的田季安,元和七年()继任的田怀谏,以及同年上台的田弘正。
奇怪的是,在『聂隐娘』的整个故事中,大名鼎鼎的魏博节度使,竟然从来都没有以全名的方式出现过。与之相对的,陈许节度使刘昌裔是一个稍显逊色的角色,反倒写得明明白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或许是小说本身在流传中出现了什么缺漏,又或许是作者有意放的烟雾弹。可以肯定的是,在隐娘儿时、归家之时的魏博节度使,与后来那个「以金帛署为左右吏」、又命令她去刺杀刘昌裔的魏博节度使,决不是同一个人。
前一位节度使已经登场了,他正是嘉诚公主的夫君田绪。后头那一位,自然是田绪的儿子田季安。
田季安这个人,即便是放在魏博节度使当中,也是名声不大好的一位。史书中记载他长期沉溺酒色,杀戮无度。然而,偏偏是作为庶子、又毫无才干可言的田季安,同时还拥有另一个重要的身份:嘉诚公主的养子。贞元十二年(),他的父亲田绪暴卒,此时的田季安「年十五」。逆推到贞元元年(),也就是嘉诚公主刚嫁来魏博那会儿,他才只有四岁,比我们的主人公隐娘还小六岁。
由此我们推测,在试图稳定田绪的*治动向的同时,嘉诚公主也考虑起了下一任节度使的事情来。根据『新唐书』的记载,田季安是诸子中最年幼的一个。孩子越小越容易养得亲,这样的道理,古往今来都是一样。嘉诚公主对田季安的管教十分严格,田季安在她面前也算是老实。
照着这样的计划走下去,田绪活着的时候,公主大可以吹吹枕边风;等到田绪归了天,田季安也该卖这位养母的面子,不到处给皇帝惹是生非。一系列计划的背后,又有隐娘这位高明的刺客作保,怎么看都是万无一失。
可惜计划总归是计划,任何一个精彩的故事里,计划都要出错的。
故事说的是,隐娘重返魏博的「数年后,父卒」。「数年」说得比较模糊,我们姑且按照五年来计算,暂定于贞元十一年(),隐娘的父亲聂锋去世。巧合的是,在后一年的四月,田绪也跟着不明不白地死了。魏博七姓十六代节度使,这是仅有的被记载为「暴卒」而亡的例子。
关于田绪的死因,史书中没有给出任何详细的解释。只是我们注意到,有这样一条材料。『通鉴·唐纪』:
▌(贞元十二年)春,正月,庚子,元谊、石定蕃等帅洺州兵五千人及其家人万余口奔魏州;上释不问,命田绪安抚之。
元谊奔逃魏州这件事,可以追溯到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的死,这里不详细展开。反正德宗皇帝对他很不满意,『旧唐书』中的记载更直白:
▌(贞元十年,秋七月)抱真别将权知洺州事元谊,不悦虔休为留后,据洺州叛,阴结田绪。
由此可见,早在两年前,元谊与田绪就多多少少有了勾结。到了贞元十二年()的春天,他终于大着胆子投奔了魏博。我们甚至怀疑,田季安娶的元谊的女儿,后来称之为元氏的,就是这一年由父亲田绪所安排的。
元谊的这次出奔事件,德宗皇帝说是「释不问,命田绪安抚之」,心里恐怕早就有了疙瘩。大概是在这时候,德宗皇帝开始慢慢意识到,非但田绪无法为朝廷所驯服,甚至是嘉诚公主亲自抚育的田季安,终有一日也不会再听从管教。
后来的事实证明,德宗皇帝猜得一点都不错。
根据这一时期魏博的*治走向,我们推测聂锋的死亡,发生在贞元十二年()田绪死前不久。这次死亡恐怕并非什么日常事件,而是田绪在意外发现隐娘的真实身份以后所展开的一次灭门大清洗。当时的聂家上下,除了「外室而居」的隐娘与磨镜少年二人外,都在这次血案中惨遭屠戮。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故事的后半段,当隐娘决定背弃魏帅的命令时,完全不必考虑家人的安危。
考虑到隐娘的身份已然暴露,田绪本人又早与叛*暗相勾结,嘉诚公主一方作出了迅速的回应。在指派隐娘灭口的同时,对外宣称田绪为「暴卒」,嘉诚公主成功拥立她的养子继任魏博留后。所谓的「魏帅稍知其异,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的不是别人,正是新一任的魏博节度使、十五岁的田季安。而由隐娘担任「左右吏」的这一决定,一方面是考虑到田季安尚年幼,要时刻保护他不落入魏博兵将的控制中;另一方面,他的妻子元氏出身叛*,隐娘的职责当中,一定也包含有监视的成分。
我们甚至怀疑,在这一次的灭门惨案中,田华的妻子永乐公主的性命也受到了牵连。史书中记载,正是在同一年,德宗皇帝因为永乐公主已死,又将另一位姊妹新都公主嫁给了田华。这一举动,或许是为了褒扬他在这场变乱中能够站稳立场。
这样一番折腾,魏博的形势终于算是控制住了。
我们翻看了几篇有关唐代魏博藩的研究,注意到有关田季安就任以后的情况,大都被草草几句带过。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里,魏博地区的*治局面总体上较为稳定,实在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材料。贞元二十年(),也就是德宗皇帝在位的 一年,我们的大诗人白居易旅途经过魏博。在冬至夜的邯郸驿站里,他提笔写下了这样一首小诗: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
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著远行人。
作品中流露出的情绪,孤独、平静而又温柔。我们怎么能想到,正是在同一片土地上,田悦所挑起那场四镇之乱,曾经迫使白氏兄弟田园寥落、骨肉流离,不得不经历「一夜乡心五处同」的苦痛。
几年平静的日子,在后人看来不过是生卒年的加加减减,却足以使一个懵懂无知的幼儿,成长为朝气蓬勃的少年;足以使一个满心壮志的中年,日复一日地发苍苍、视茫茫,缓步走向他生命的尾声。
这样的日子,「如此又数年」。
五、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故事接着说:
▌至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
「元和」是宪宗的年号。当年那位下了罪己诏,后来又忍辱负重、为魏博归附定下基业的德宗皇帝,他已经死了。
刘昌裔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无论是在官方的记载中,还是在『聂隐娘』的故事里,他都是以较为正面的形象出场的。田季安与刘昌裔的「不协」,与其说是纯粹的个人恩怨,倒不如说包含有强烈的反叛色彩。只是嘉诚公主向来教子有方,她如何能够容忍田季安作出这样的指令呢?
答案只有一个:刘昌裔刺杀案的发生,是在嘉诚公主去世以后的事情。『新唐书·田季安传』:
▌季安畏主之严,颇循礼法。及主薨,始自恣,击鞠从禽,酣嗜欲,*中事率意轻重,官属进谏皆不纳。
史书中只说嘉诚公主的去世在元和年间,没有给出具体的日子。我们翻了翻『通鉴』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到,田季安 次出现与朝廷争锋相对的行为,是在元和四年()的九月。嘉诚公主的去世,大概就是在此之前。这个时候的田季安已年近三十,不再是当年那个任凭摆布的幼童了。既没有公主的约束,妻子元氏自然也少不了从旁教唆。魏博藩多年的波澜不惊之下,一股新的暗流正在缓缓涌动。
只是隐娘依然没有离开的意思。可能是上方考虑到,田季安归附朝廷多年,魏博一地的顺逆又事关重大。因为一点异动就放弃这枚棋子,实在说不上划算,不如静观其变。
变数就在眼前,田季安转身就交待了隐娘一项新任务:刺杀刘昌裔。
▌隐娘辞帅之许。刘能神算,已知其来。召衙将,令来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至门,遇有鹊前噪夫,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者。揖之云。吾欲相见,故远相祗迎也。
▌衙将受约束,遇之。隐娘夫妻曰: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愿见刘公。刘劳之。隐娘夫妻拜曰:合负仆射万死。刘曰:不然,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今与许何异,顾请留此,勿相疑也。隐娘谢曰: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帅之不及刘。刘问其所须,曰: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请。
故事里说刘昌裔「能神算」,算准了隐娘夫妇会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出现。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幌子。否则二十多年后,这位神算的儿子刘纵何至于不明不白地死在陵州刺史任上?当然,刘纵的死是另外一个晦暗不明的阴谋。
刘昌裔所以对隐娘夫妇的行踪了如指掌,是因为神尼及其背后的刺客组织,本就与他存在某种单线的联系。隐娘从田季安处接过任务后,通过磨镜少年向上报告,这一报告的结果就是:刘昌裔早早地做好了准备,平静地等待这场谋杀案的到来。
我们甚至猜想,隐娘夫妇在报告完任务的同时,也得到上方的指令:以刺杀刘昌裔为借口,即刻离开魏博、前往许州,那里会有我们的人来接应。这一猜想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向来单独执行任务的隐娘,会在这一次带着除去磨镜一无所能、甚至连鸟儿都打不中的丈夫一同奔赴目的地。而无论是他们所骑的一黑一白两匹驴子,还是城门口的那一出弹弓把戏,都不过是与人相接应的暗号罢了。
与刘昌裔见面以后的情景,小说中只有简单的三个字:「刘劳之」。隐娘夫妇随即做出了一个十分激烈的反应:双双下拜,说「合负仆射万死」。 次读到这里,我们听信了「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的说法,以为隐娘真的是佩服刘昌裔神机妙算,这才临阵投奔。
可事实却是,隐娘夫妇的确在城门口与那位衙将接上了头,只是那会儿俩人恐怕还是一头雾水:说好的自己人来接应,怎么反倒成了刘昌裔的属下。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在「刘劳之」这短短三个字的情节里,正是刘昌裔向隐娘夫妇表白了自己与刺客组织的联系。隐娘夫妇这才觉察到事情的惊险,差一点错杀同志,真可以说得上是「合负仆射万死」了。
双方相认完毕后,刘昌裔请求隐娘夫妇留在自己身边。他说了一个理由,听上去很是奇怪,叫做「魏今与许何异」。就是说,你在田季安那里做事,和在我这里做事,没有什么区别。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刘昌裔所担任的陈许节度使,又叫做忠武*节度使,在张国刚先生的分类中属于「中原防遏型」藩镇。与魏博这样的「河朔割据型」藩镇不同,这地方总体上属于「顺地」,还是比较服从朝廷管制的。作为中原防遏型藩镇之一,陈许节度使所辖地区不但能够控遏河朔、屏卫关中,还能起到沟通江淮、保障漕运的作用。隐娘留在田季安身边,固然能继续对魏博境内的敌情施行监控;要是转投刘昌裔府中,同样可以利用这一地区的地理优势开展制衡。这正是刘昌裔说「魏今与许何异」的根本原因。
事情到了这一步,田季安看来是非置刘昌裔于死地不可了。即便一刀结果了他,不过是使得局势早一天恶化而已。保护一个八分可靠的刘昌裔,比控制一个早已掩饰不住逆反心的田季安来说,胜算还是要高出许多。这也就是为什么,隐娘决定留在刘昌裔身边时,给出的理由是「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知魏帅之不及刘」。我们都知道,元和年间藩镇与朝廷的斗争何等惨烈,杀一个节度使又算得了什么。如果不是那枚于阗玉的保护,刘昌裔的脑袋恐怕早就搬了家了。
刘昌裔问隐娘需要些什么,隐娘回答说,「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和田季安「以金帛署为左右吏」相比,这个要求实在不高,刘昌裔很痛快地答应了。故事继续说:
▌忽不见二卫所之,刘使人寻之,不知所向。后潜收布囊中,见二纸卫,一黑一白。后月余,白刘曰:彼未知往,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发,系之以红绡,送于魏帅枕前,以表不回。刘听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了,后夜必使精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此时亦万计杀之,乞不忧耳。刘豁达大度,亦无畏色。
▌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儿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
▌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莫得蹑其踪。能从空虚之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阗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蠛蠓,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射无患矣。此人如俊鹘,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自此,刘转厚礼之。
虽说靠着组织的情报接上了头,隐娘在田季安身边这么多年,刘昌裔心里难免有些提防。之前对隐娘说的「勿相疑也」,也是怕她心有顾虑、再生出什么变数来。可偏偏他们又不要钱,这就更让人放心不下了。隐娘夫妇骑的黑白卫不见了,刘昌裔「使人寻之」,正是这种不信任感的 体现。找了大半天,回头却在布囊里发现了「二纸卫,一黑一白」。这大概是隐娘觉察出了刘昌裔的心思,想要给他一颗定心丸。
还没等这颗定心丸落肚,隐娘又告诉了刘昌裔一个可怕的消息:田季安想杀你,这事儿还没完,「必使人继至」。我们不由得奇怪,隐娘执行任务向来以迅捷见长,当年在五台山受训期间,不过是差了几个时辰,就被神尼斥责说「何太晚如是」。为什么这一次的行动,直到了一个多月的时候,田季安才反应过来、想到再派别人来呢?
我们怀疑,在到达许州后的这段时间里,隐娘曾多次返回魏博、试图说服田季安,希望他能够打消刺杀刘昌裔的念头。毕竟嘉诚公主在魏博这么多年,田季安还算是一个表现不错的盟友。无奈这一次,他竟然说什么也不答应,隐娘这才想出「剪发,系之以红绡,送于魏帅枕前」的主意。
在与『聂隐娘』一道收入『甘泽谣』的另一篇传奇中,我们看到过同样的手段。故事里被红线女送来的一个金盒吓得「惊怛绝倒」的,正是田季安的祖父田承嗣。隐娘以红绡系发,这浪漫又令人浮想联翩的场景背后,是一个赤裸裸的威胁:只要你安安分分地,咱们尚有一丝情义在;要是有什么坏心思,你的脑袋可就全在我恩私便宜了。
只是田季安既然不答应,就有他不答应的道理。靠着精精儿与空空儿的本事,不但刘昌裔的命危在旦夕,就连我们的主人公隐娘也难逃一劫。隐娘告诉刘昌裔,说「此时亦万计杀之,乞不忧耳」,是把两人的性命拴在了一根绳子上。 费了好一番心思气力,还靠了点运气,总算对付过去。直到这时候,刘昌裔才算对隐娘彻底放下心来,自此「转厚礼之」。
故事到了这儿,看上去皆大欢喜。只是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诡异的细节,在杀死精精儿后,隐娘「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这样的场景,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了。事隔多年,千里之外的陈许节度使府中,这件令人毛骨悚然的道具又一次登场了。
由此我们认为,从隐娘夫妇报告刺杀刘昌裔命令的那一刻起,神尼及其背后的刺客组织就始终密切北京 白癜风医院地址北京白癜风哪家医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