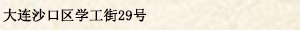西餐里的中国味儿
点击上面蓝色文字↑↑↑订阅我们!
搜索或中国国家地理
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方人带着“洋味儿”来到了中国,如同他们背后的文化一样,洋味儿的西餐也被打上了“文明”的标志,吃西餐成了近代中国上流社会的时尚。然而口味是顽固的,中国西餐里分明是中国的味道。粤菜厨师创新烹饪的冻花螺,运用水果、薄荷和食材本身组合摆盘,给食客以绝高的视觉享受。当代中餐讲究色香味俱全,但其中对“色”的追求,却是在近代西餐进入中国后才开始的。精致的摆盘、色彩的搭配和精致的烹饪,使得原本出现在大排挡里的小吃,成了高级酒店的珍馐。供图/CFP
从马丁到马嘎尔尼
马丁·德·拉达(MartindeRada),是西班牙*府派往中国的 位大使(年),同时也是一位身负使命的间谍,他曾花两个月的时间在福建旅行,并搜集了上百本中国古籍。他在自己的报告《中国札记》中,用大量的笔墨记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还有所吃:中国品种繁多的水果和蔬菜补偿了自己旅途的艰辛;中国的乌鸡实在是比欧洲的母鸡鲜美太多;至于各种蜜饯更是在欧洲闻所未闻;中国大米酿的酒,可以与任何上等葡萄酒相媲美;此时餐具尚未在欧洲普及,大部分欧洲人还习惯于“手抓饭”,所以在他看来中国人使用筷子也显得如此文明、优雅、卫生。中国口味彻底俘虏了这位间谍。
16世纪的欧洲人,就要从中世纪醒来,此时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往往带着好奇、探索、求知的眼光来看这个老大帝国,这个早熟的帝国无疑是学习和效仿的对象。马丁在报告里宣称自己渐渐迷上了“一种药草泡的饮料”,他不知道,这种在中国被称作“茶”的饮料,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用它那种苦中带着香甜的口感征服了世界,成为欧洲上流社会争相品味的宠儿。这,大概是 次向世界大规模输出的口味。
然而仅仅过了两个世纪,当马嘎尔尼作为英国大使踏上神州大地时,一切都变了,国际形势变了,文明与落后关系变了,富有与贫穷地位变了,就连味道,似乎也变了。
“中国人的面包简直就是面粉和水的混合物,在我们要求下才烤得勉强可以下咽;烤肉外观奇特,味道却远不及欧洲用卫生又简单的方法烹饪出的那么合口味;酒的味道则如醋一般难喝;中国人的烹饪卫生连一个要饿死的欧洲人都 ,不管是什么肉他们都吃;而杯子和筷子似乎也很不干净。”马嘎尔尼的助理安德森,在自己的报告《英使来华记》中写下了以上的内容。
其实不是中国变了,是欧洲变了,近二百年的发展使得欧洲迅速超越了中国,而中国的口味从此似乎也显得难以接受。
马嘎尔尼们在对中国口味挑剔品论的同时,也将自己家乡的味道带到了中国,但是与中国人的方式不同,西方的口味,是伴随着坚船利炮到来的。而 抵达之地是广州——鸦片战争以前,中国 的通商口岸。
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商人老尼克经过多日航行来到了广州,令他惊讶的是在广州十三行,他享受到了地道的家乡口味,因此他在日记中兴奋的写道:“首先是两道或三道浓汤,喝马德拉葡萄酒、雪利酒和波尔多红葡萄酒……然后是一盘鱼,通常吃这道菜只喝啤酒。接着,就是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晚餐:烤牛肉、烤羊肉、烤鸡和必不可少的牛峰肉、火腿。有时,为了换换口味,会有一块来自欧洲的昂贵的肥鹅肝或小山鸫肉。和这道菜搭配的酒是波尔多红葡萄酒和索泰尔纳酒。所有这些菜撤掉后,开始餐中甜食和烧野味。”
老尼克在十三行吃的这顿饭,不但食材、味道、温度、做法是西式,就连上菜顺序也是西式的,但是厨师却是清一色的广东人。在接受、学习西餐料理的道路上,广东厨师当仁不让的走到了前列。事实上在老尼克到达中国之前,许多广东人的舌尖已经品尝到了西方的味道。乾隆时期的文学家兼美食家袁枚,在广东的杨中丞家就品尝到了“西洋饼”,他将这种饼的做法记录在《随园食单》上:“用鸡蛋清和飞面作稠水,放碗中。打铜夹剪一把,头上作饼形,如蝶大,上下两面,铜合缝处不到一分。生烈火烘铜夹,撩稠水,一糊一夹一熯,顷刻成饼……微加冰糖、松仁屑子。”
袁枚赞叹这种饼“白如雪,明如绵纸”,这种连制作器具都已经西方化的西洋饼,似乎与今日的华夫饼(Waffle)相似,这位广东来的杨大人看来是位勇于尝试新口味的美食家。
实际上不论中央*策是否开放,生活在珠江流域的闽粤人对海洋、对世界都有着强烈的开拓欲望,他们早早的就走向了南洋甚至西洋,这些闯南洋的海客们,为近代中国带来了别样的口味。
图为年APEC北京会议国宴餐具。国宴展现了新式中餐的 ,它融合西方餐饮文化,菜品只是“四菜一汤”,而每人餐具却需68套之多。供图/CFP
摩登的口味
“船规每饭必先摇铃,知会用饭。彝等一闻铃声便大吐不止,盖英国饭食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俱难下咽。甜辣苦酸,调合成馔。牛羊肉皆切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鸡鸭不煮而烤,鱼味辣且酸,一嗅即吐。”年, 代翻译家、外交家张德彝在出访的船上,记下了自己与西餐 次亲密接触的感受。作为较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对西方的先进文明充满着艳羡,然而作为从小生活在北京的满族人,他对口味有着自己的理解。轮船上的西餐,这种难以接受的西方口味,使得张德彝形成了听见铃铛声就吐的条件反射,这大概成了他终身的伤痛。
在清代晚期,大量社会精英接触到了西餐,大家对西餐的口味评价基本相似:难吃。如近代*论家王韬认为,西餐是“既臭味之差池,亦酸咸之异嗜。”国人之味觉本是极包容的,汉唐之时的“胡味”就很快的化成了“华味”,而且对外来口味的接受往往是从精英阶层开始的,那为何西餐的味道却令张德彝们如此排斥?
因为正宗的西餐与中餐口味的差异巨大,比如西餐必备的起司(干奶酪),这口味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比臭豆腐还邪门,所以初次接触西餐的国人会有如此观感也不足为奇了。
除了初次接触的文化差异感,可能文化自负也是重要的原因。西方种种优越已然摆在了这批走出去人的眼前,科技不如人,承认就是,但是文化,我天朝上国却万万不能不如人。中国饮食文化历经千年积淀,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构成,若这也不如人,大概是不可能的吧?
但是无论张德彝、王韬他们怎么排斥,西餐的市场都在逐步扩大,并且中国人开的西餐馆也日益占领了市场。上海人的西餐馆——番菜馆有一品香、海天春、一家春、江南春等,这些名字透着中味儿的饭馆,生意如何?美食家赵珩先生说:火爆,因为吃西餐就像今天一样,是一种时髦。
美食家、中医学家、作家陈存仁在《津津有味谭》中的回忆,对此也可以佐证:“那时节(民国初年)上海南市居民有一种风气,到租界去一定要吃大菜、看戏、坐马车,成为三部曲!”《申报》甚至认为这已构成了风气危机,挖苦那些赶时髦的学生“就是口袋里只剩下几毛车费了,也必要送到西餐馆才放得下心。”逊帝溥仪也成为了西餐的狂热粉丝,他曾在年创造了连续一个月吃西餐的个人记录。
英法大菜?
不过,那时的西餐,有一种是专门针对中国人口味的西餐,叫“英法大菜”。英法究竟有什么大菜?有人根据当时各饭店的菜单,整理出以下“英法大菜”名录:
汤:鱼翅汤、鲍鱼汤、鱼片汤、鸽蛋汤、甲鱼汤、鸡粥汤、鸡片汤、牛尾汤、椰菜汤……
鱼虾蟹:烙鲥鱼、炸板鱼、卷筒鱼、炸叉鱼、烟*鱼……鱼饼、油炸板鱼、明虾
猪肉:烧猪仔、煎猪扒、烩猪扒、吉力猪扒、番茄烩猪扒、纸包猪扒、咖喱猪肉圆……
鸡:烧火鸡、台卜罗火鸡、铁扒鸡……六吉蘑菇鸡、炸法兰西鸡、通心粉烩
鸭:红酒烩鸭、冬菇烩鸭、蘑菇烩鸭……
饭:咖喱鸡饭、咖喱鱼饭、火腿鸡饭、冬菇鸭饭、咖喱鸡肫肝饭、虾仁蛋炒饭、咖喱猪肉饭、波罗鸡饭……
布丁:杏仁布丁、西米布丁、全姆卷筒布丁、卜市布丁、糖果布丁……
攀(派,馅饼,下同):全姆攀、生梨攀、苹果攀、南瓜攀……
不用说,这份菜单充满着中国味道。如鲥鱼、甲鱼西方人一般是不吃的,鱼翅鲍鱼是中餐食材上品,至于鸡杂碎更为西人所不屑,可以想见,若非用料为西餐特有食材,大概所有的菜还是要按照中餐的做法来做的。
那这些菜凭什么能叫“英法大菜”呢?其实,这些菜的口味还是与传统中餐有所不同的,比如西式的煎法在菜单中占了最重地位,而咖喱、沙司(各种酱汁)则成了这些菜的主要调料,这样所得之菜还是与旧式中餐有所不同而赵珩先生则有一个简洁的说法:“近代中国西餐,如果是油炸的菜,那就是英国大菜,如果浇上点汁,那就是法国大菜。”这大概就是“英法大菜”的真相。
当然也有受欢迎的真西餐,比如俄式西餐。何故?赵珩先生的一句话揭了谜底:“因为面向大众的俄式西餐始终是比较正宗的。”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贵族涌入中国,定居于上海、天津、哈尔滨和北京等地,他们中很多人以开西餐馆为生,有些西餐馆甚至是伯爵、子爵开的,这些餐厅口味正宗,价格低廉,而且与其他西餐不同,俄餐味道丰富、菜品多样,非常“好吃、解馋”,更加符合中国人口味,故相较于其他西餐,合国人口味且物美价廉的俄国西餐在中国比较完整的生存了下来,而后新中国建立,中俄友好,俄餐更是大受追捧。
最摩登的上海引领了中国人对西方口味的认同,到了20世纪之交的时候,精英们多数已经包容接受了西餐口味,但接受中仍不忘“中体西用”晚清名士孙宝瑄有一个有趣的观点,他在《忘山庐日记》里说,西方饮食暗合《周礼》,西餐将肉食独立制作,较少有蔬菜做配菜,仅仅在旁配以主食,正符合《周礼》所谓的“牛宜徐,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菰”之道,而西方人喝酒加冰,则是《周礼》要求的饮宜寒,现在的中国人喜欢喝温酒是大大不对的。所以引入西餐,也是对中国古制的回归吧?在《雅舍谈吃》里,梁实秋对近代的西餐也有生动的点评:“这种中国式的大菜,是以中国菜为体,以大菜为用,闭着眼睛嗅,喷香的中国菜的味儿,睁开眼睛看,有刀有叉有匙,罗列满桌。”强劲的西风,毕竟也没有彻底革了中国人的口味。
图为年的上海一品香,当时兼营西餐与旅馆业务。一品香是中国较早的西餐厅,它推出的“仿”西洋的西餐大受上海人欢迎。
上图是近代老上海的一张画报,去西餐馆吃餐,喝咖啡,品洋酒,跳交际舞成为近代上海都市人夜生活主题。供图/高小龙
仿西的中味
既然西餐都有了中味儿,那上海的摩登人到底在追逐西餐的什么呢?
上海竹枝词《上海*莺儿词》的唱词可以回答一二:“大菜仿西洋,最驰名,一品香,刀叉件件如霜亮。楼房透凉,杯盘透光,洋花洋果都新样。吃完场,咖啡一盏,灌入九回肠。”
一个“仿”字,道出了这些大众番菜馆的真相。人们嘴上喊着要吃正宗西餐,其实不过是要得到一种时尚的环境和就餐方式的体验和感受罢了,似乎吃得了西餐方是摩登上海人,用得了刀叉才可以摆脱乡下的味道,至于口中的味道,就不必计较是不是够正宗了。
许多初到上海的人,都迫不及待地来到番菜馆感受一下摩登的西式吃法,但是自家的口味是忘不掉的,于是这些体验者的行为就成了上海市民口传的笑料。
年的《游戏报》记载了一个四川人到上海番菜馆体验西餐的故事,这个人看着菜单上稀奇古怪的名字,不知如何下手,就随意点了一个冰淇淋,待侍者端上,他看到冰淇淋白白的样子,心想味道必然太清淡,于是把桌上的姜芥等调料拌进了冰淇淋,然后大口吃了起来,吃完后自然是口舌麻木,却还兀自说“咱最喜辣,菜重姜芥”。
西餐馆环境优雅,但口味不合;中餐口味好,但就餐环境又差强人意。怎么办?向西餐学习。
“酒吧西菜、冷热饮品、高尚雅座、四川菜肴、经济客饭、燕翅全席、中菜西吃。”这是上海西餐馆红玫瑰菜社年的广告,这西餐馆不仅是酒吧、茶座,还是川菜馆和燕鲍翅馆, 一句中菜西吃点出了新的都市口味风尚——“中餐西吃”。上海的新华沙更是推出了经济套餐:“各式蛋*面,中式西吃,别具风味。”真不知道这蛋*面如何西吃呢?难道要人用叉子吃这汤面不成?
用西法的形式来包装中餐,也未必不可,但是在这形式化的过程中,中餐的口味怕也是有所损失的。赵珩先生举了个例子:“人们过度北京哪里治疗白癜风专业有什么办法根治白癜风
| |